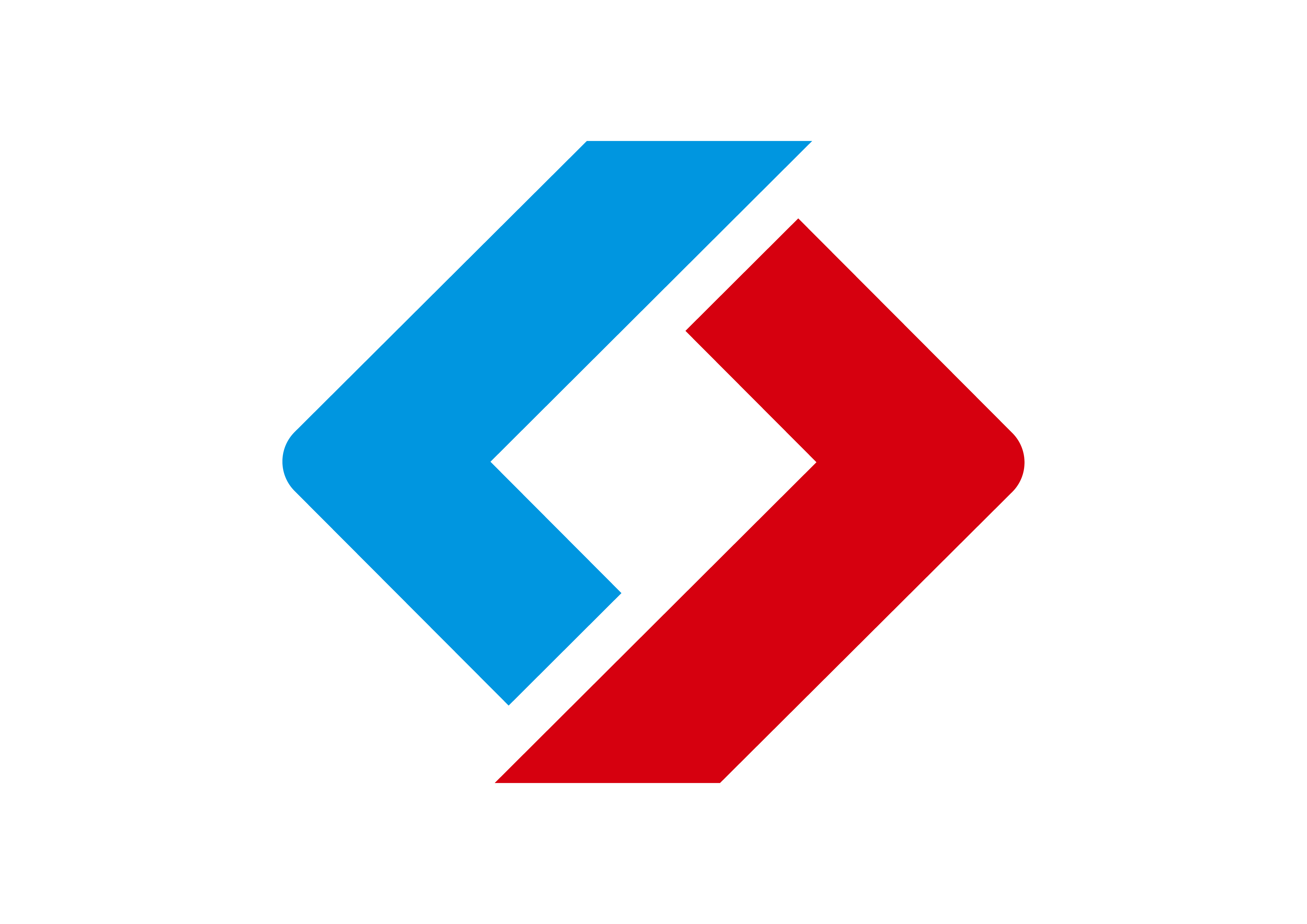- ģĒ«įőĽ÷√£ļ
- ◊Ūď > ťLļ£ĹŐ”żĆ£ôŕ > ÷ųĺéÕ∆ň]
ő“◊Ó”ĎÖíĶńń«āÄ‘~
įl(f®°)≤ľ’Ŗ£ļcj_ysh įl(f®°)≤ľērťg£ļ2013-12-27 16:09:06 ŁcďŰĒĶ(sh®ī):
°∂÷–áÝ«ŗńÍąů°∑£®2013ńÍ12‘¬24»’£©
ļň–ńŐŠ ĺ
‘ŕ…ÁēĢ…ķĽÓ÷–£¨ŅŐįŚ”°ŌůĪ»Ī»Ĺ‘ «£¨Ī»»Á“ļ√ĆW…ķ”ĺÕ «“÷ĽēĢ◊xēÝ”°Ę“Ō≤ögģĒņŌéüĶńĆôÉļ”£Ľ“ŅŅ◊V”ĺÕ «“¬†‘í”°Ę“ōďōü»ő”£Ľ“ļ√»ň”ĺÕ «“≤Ľ÷v‘≠Ąt”°Ę“ń®Ō°ńŗ”°Ę“üoń‹”……’f’Ŗ“≤‘S≤Ęõ]”–“‚◊RĶĹŖ@–©ŅŐįŚ”°Ōů£¨¬†’ŖÖsń‹ĹYļŌ◊‘ľļĶń…ķĽÓ≠h(hu®Ęn)ĺ≥ļÕ–ńņŪůwÚě£¨√Űł–Ķō“įl(f®°)ĺÚ”≥ŲŃŪÓźĶń““‚Ńx”°£”–ērļÚ£¨ő“āÉŖÄēĢ÷ųĄ”ĶōőŁ ’Ŗ@–©ŃŪÓźĶń“‚Ńx£¨’JěťňŁ’śĶń «◊‘ľļĶń“Ľ≤Ņ∑÷£¨∂Ý«“ «≤Ľļ√Ķń“Ľ≤Ņ∑÷°£”ŕ «£¨ő“āÉÖĘŇcĶĹ◊‘ő“Ĺ®ėč÷–°£
ėňļěüoňý≤Ľ‘ŕ£¨ő“āÉ”÷≤Ľń‹∂¬◊°Ąe»ňĶń◊ž°£Ķęľ»»ĽŖ@–©ėňļěĶń“‚ŃxŅ…“‘ĪĽĹ®ėč£¨ń«√īňŁ“≤Ņ…“‘ĪĽĹ‚ėč≤ĘĪĽ÷ō–¬Ĺ®ėč°£ń„Ņ…“‘į—ňŁ“ēěť“’`◊x”°Ę“∆ę“䔣¨“≤Ņ…“‘į—ňŁ“ēěť“ŐŠ–—”°Ę“ļŰÜĺ”°£
ÍĎē‘čI
ĻĢ£¨ģĒő“ ‹ĺé›č—Żľsť_ ľĄ”ĻPĆĎŖ@āÄŁc‘uēr£¨ő“įl(f®°)¨F(xi®§n)◊‘ľļĶŰŖMŃň“ĽāÄŌ›ŕŚ°£ő“∑¬∑ūŅīĶĹ◊x’Ŗ÷TĺżĪ†÷Ýļ√∆ś°ĘÓB∆§Ķń—Řĺ¶ÕŻ÷Ýő“’f£¨ļŔ£¨ń„£¨ÍĎē‘čI£¨ń„◊Ó≤ĽŌ≤ögĄe»ň’fń„ ≤√ī£Ņ
ļ√į…£¨ļ√į…£¨ĺÕ◊Ćő“Źń◊‘ľļĆĎ∆ūį…£°
īůńX…ŮĹõ(j®©ng)‘™ť_ ľ∑ŇŽä£¨≤ĽĶĹįŽ√ŽÁäĶńĻ§∑Ú£¨ń«āÄ‘~ĺÕ≥Ų¨F(xi®§n)Ńň£¨ŖÄįťŽS÷Ýűr√ų…ķĄ”ĶńąŲĺį£ļń« «‘ŕ–ńņŪ›oĆß≤© Ņįŗ…Ō£¨ő“āÉ∑÷≥…–°ĹMáķ»¶∂Ý◊Ý£¨Ń÷√Ō∆ĹĹŐ ŕ“™ő“āÉŌ»‘ŕ“ĽŹą–°ľąól…ŌĆĎŌ¬◊‘ľļĶń√Ż◊÷£¨»ĽļůŪėērŠėāųĹoŇ‘ŖÖĶń»ň£¨’ąňŻāÉ”√“Ľ–©‘~√Ť Ųƶń„Ķń”°Ōů°£ģĒ–°ľąól◊ÓļůĽōĶĹ◊‘ľļ ÷…Ōēr£¨“™ŐŰ≥Ų◊‘ľļ◊ÓŌ≤ögļÕ◊Ó≤ĽŌ≤ögĶń°£ő““Ľ—ŘĺÕŹń÷T∂ŗ–ő»›‘~÷–ŐŰ≥Ųő“◊Ó≤ĽŌ≤ögĶń£ļ“ĺęł…”°£
ő“£¨“ĺęł…”£Ņĺę√ų”÷Źäł…£ŅŖ@ «ő“ÜŠ£Ņő“ļ‹…ĶŇ∂£¨∂Ý«“Ąe’fŹäł…£¨ŖBń‹ł…∂ľň„≤Ľ…Ō°£
ő“≤ĽŌ≤ögŖ@āÄ‘~£¨’śĶń≤ĽŌ≤ög°£
Ķę£¨ěť ≤√ī≤ĽŌ≤ög£Ņ «“ÚěťňŁ≤ĽŌŮő“£ŅŖÄ «“Úěťő“ŹńŖ@āÄ‘~…Ō◊x≥ŲŃňŃŪÕ‚Ķń“‚ňľ£Ņ
ļ√į…£¨ő“≥–’J£¨≥żŃň”XĶ√≤ĽŌŮ◊‘ľļÕ‚£¨∆šĆćő“’śĶń◊x≥ŲŃňĄeĶń“‚ňľ°£“ĺęł…”£¨ĺÕŌŮ“ĽÓwťL≥ŲŐŔ¬ŻĶń∑N◊”£¨ŪėŐŔ√ĢĻŌ£¨ő“◊xĶĹĶń «“ŇģŹä»ň”°Ę“»Ī∑¶»Š«ť”°Ę“÷ĽÍP◊ĘĹYĻŻ”°Ę“Ŗ^”ŕņŪ–‘”Ķ»Ķ»Ķ»Ķ»°£ń„āÉ’f£¨ő“ń‹Ō≤ögÜŠ£Ņ
«ő“…Ū…Ō’śĶń”–“ĺęł…”∂Ý◊‘ľļÖs≤Ľ÷™Ķņ£ŅŖÄ «ń«Õ¨ĆWį—ňŻ◊‘ľļõ]”–ÖsŅ ÕŻďŪ”–ĶńŐōŔ|(zh®¨)Õ∂…šĶĹŃňő“…Ū…Ō£¨ĺÕŌŮ“ĽāÄ»ňŅ Ńň£¨Ös√¶÷Ý읥e»ňīÚňģ“Ľė”£Ņ“÷ĽÚ «»ňľ“’żĹõ(j®©ng)Éļ’Jěť“ĺęł…” «āÄįżŃx‘~£¨∂Ýő“Ös»ő“‚∑Ňīů°Ęҧ«ķŃň“ĺęł…”Ķńļ¨Ńx£Ņ»ÁĻŻ «Ŗ@ė”£¨ « ≤√īѶŃŅ◊Ćő“Ŗ@√ī◊Ų£Ņ
Ŗ@√īŌŽ÷Ý£¨ĺÕļ√ŌŮŖM»ŽŃňĪĪĺ©ĶńžFŲ≤÷–°£
”√ā•īůĶń÷‹ĻĢņÔ£®Johari Window£©÷ģīįń‹Ĺ‚ŠĆÜŠ£Ņ–ńņŪĆWľ“ŰĒ∑ÚŐōŇc”ĘłŮĚhį—»ňĶń◊‘ő“∑÷≥…“ĽāÄ2×2ĶńĺōÍᣨĺÕŌŮ“Ľ∂¬Č¶…Ōť_Ńňňń…»īįĎŰ°£Ķŕ“Ľ…»īįĎŰņÔĶń“ő“”£¨ «ő“÷™Ķņ°ĘĄe»ň“≤÷™ĶņĶńń«≤Ņ∑÷“ő“”——“ť_∑Ňő“”£ĽĶŕ∂Ģ…»īįĎŰņÔĶń“ő“”£¨ «◊‘ľļ÷™Ķņ£¨Ąe»ň≤Ę≤Ľ÷™ĶņĶń“ő“”——“Ž[≤ōő“”£ĽĶ໿…»īįĎŰņÔĶń“ő“” «Ąe»ňŅīĶ√ĶĹ£¨ő“◊‘ľļÖs≤Ľ÷™ĶņĶń“ő“”——“√§ńŅő“”£ĽĶŕňń…»īįĎŰņÔĶń“ő“” «ő“◊‘ľļļÕĄe»ň∂ľõ]”–įl(f®°)¨F(xi®§n)Ķń“ő“”——“őī÷™ő“”°£
ń«√ī£¨“ĺęł…” «‘ŕ“√§ńŅő“”ĶńīįŅŕņÔÜŠ£ŅĄe»ňŅī“äŃň£¨ő“◊‘ľļÖs≤Ľ÷™Ķņő“”–Ŗ@ė”ĶńŐōŔ|(zh®¨)īś‘ŕ£Ņ»ÁĻŻį—◊‘ľļ“Ľ∑÷ěť∂Ģ£¨◊Ć“ĽāÄ“ő“”Ôhł°∆ūĀŪ»•”^≤ž‘ŕĶō…ŌĶńń«āÄ“ő“”£¨ēĢŅī“ä ≤√īńō£Ņļ«ļ«£¨Ôhł°∆ūĀŪĶń“ő“”Ņī“äŃňĶō…ŌĶń“ő“”’żľ≤◊Ŗ»ÁÔL£¨’f‘íļÜ∂Ő£¨≤ĽŌ≤ögÜ™ŗ¬£¨”√“∂ŗ»őĄ’ń£ Ĺ”Õ¨ērŐéņŪé◊ŪóĻ§◊ų£°Ŗ@£¨ń‹’f≤Ľ «ő“ÜŠ£Ņ“≤‘S£¨ĺÕ «Ŗ@–©Õ‚‘ŕĶń––ěťŐōŁc£¨◊Ćń«āÄÕ¨ĆW’Jěťő“ļ‹——ĺęł…°£
‘ŕňŻĶń‘~Ķš÷–£¨“ĺęł…”Ď™‘ď≤Ľ «“ĽāÄŔHŃx‘~£¨Ķęěť ≤√īő“ĺÕ «≤ĽŌ≤ögńō£Ņ
◊Ćő“‘ŔĶĹ’‹ĆWľ“°Ę’Z—‘ĆWľ“ń«ņÔ’“’“’fřo°£
ő“’“ĶĹŃňĺSŐōłýňĻŐĻ£¨Ŗ@āÄ≥šĚMāų∆ś…ę≤ Ķń»ňőÔ£¨ĪĽ∑Qěť“’Z—‘’‹ĆW”ĶńĶžĽý»ň°£ňŻ’Jěť‘~’ZļÕ––Ą”°Ę ¬őÔ°Ę≠h(hu®Ęn)ĺ≥ «üo∑®∑÷ť_Ķń£¨“’Z—‘Ķń“‚ŃxĀŪ‘ī”ŕ∆š‘ŕő“āÉ∂ŗ∑N∂ŗė”…ķĽÓ–ő Ĺ÷–Ķń–ß”√”°£
ļ√į…£¨◊Ćő“į—≥ťŌůĶńłŇńÓŖÄ‘≠ĶĹĺŖůw«ťĺ≥÷–ĀŪ°£‘ŕĺSŐōłýňĻŐĻń«ņÔ£¨“ĺęł…”Ŗ@āÄ‘~õ]”–≥ťŌůĶń“‚Ńx£¨ĪōŪö∑ŇĶĹ≠h(hu®Ęn)ĺ≥÷–»•Ņľ≤ž°£ňŁÕ®≥£ēĢ≥Ų¨F(xi®§n)‘ŕńńņÔńō£ŅŅŌ∂®≤Ľ «ľ“Õ•ņÔļÕ–›ťeąŲňý£¨∂Ý «¬öąŲ…Ō°£◊ųěť“ĽāÄƶĻ§◊ųĪ»›^Õ∂»ŽĶń¬öėI(y®®)Ňģ–‘£¨»ňāÉÕ®≥£ēĢ”–Ŗ@ė”ĶńŅŐįŚ”°Ōů£¨Ī»»Á≤ĽÓôľ“°Ę…Ŕ«ť»§°ĘŐęņŪ–‘Ķ»°£ňÕĹoő“Ŗ@āÄ‘~Ķńń–Õ¨ĆW£¨Ć¶īň÷–ĶńőĘ√ÓҬ «Žy“‘ůwēĢ°£
’Z—‘ĆWľ“āÉńō£ŅňŻāÉ’f£¨ń„¬†ĶĹĶń≤ĽÉH «“ĽāÄ‘~Ķń¬ē“Ű£¨Ī»»Ájinggan£¨ń„ŖÄēĢ“¬†≥Ų”Ŗ@āÄ‘~Ķń“‚Ńx°£“≤ĺÕ «’f£¨√ŅāÄ»ňƶ“¬†ĶĹ”Ķń–ŇŌĘŖM––Ĺ‚īaēr£¨∂ľēĢěťňŁĹ®ėčĆŔ”ŕń„Ķń“‚Ńx°£
‘ŕ…ÁēĢ…ķĽÓ÷–£¨ŅŐįŚ”°ŌůĪ»Ī»Ĺ‘ «£¨Ī»»Á“ļ√ĆW…ķ”ĺÕ «“÷ĽēĢ◊xēÝ”°Ę“Ō≤ögģĒņŌéüĶńĆôÉļ”£Ľ“ŅŅ◊V”ĺÕ «“¬†‘í”°Ę“ōďōü»ő”£Ľ“ļ√»ň”ĺÕ «“≤Ľ÷v‘≠Ąt”°Ę“ń®Ō°ńŗ”°Ę“üoń‹”……’f’Ŗ“≤‘S≤Ęõ]”–“‚◊RĶĹŖ@–©ŅŐįŚ”°Ōů£¨¬†’ŖÖsń‹ĹYļŌ◊‘ľļĶń…ķĽÓ≠h(hu®Ęn)ĺ≥ļÕ–ńņŪůwÚě£¨√Űł–Ķō“įl(f®°)ĺÚ”≥ŲŃŪÓźĶń““‚Ńx”°£”–ērļÚ£¨ő“āÉŖÄēĢ÷ųĄ”ĶōőŁ ’Ŗ@–©ŃŪÓźĶń“‚Ńx£¨’JěťňŁ’śĶń «◊‘ľļĶń“Ľ≤Ņ∑÷£¨∂Ý«“ «≤Ľļ√Ķń“Ľ≤Ņ∑÷°£”ŕ «£¨ő“āÉÖĘŇcĶĹ◊‘ő“Ĺ®ėč÷–°£
ėňļěüoňý≤Ľ‘ŕ£¨ő“āÉ”÷≤Ľń‹∂¬◊°Ąe»ňĶń◊ž°£Ķęľ»»ĽŖ@–©ėňļěĶń“‚ŃxŅ…“‘ĪĽĹ®ėč£¨ń«√īňŁ“≤Ņ…“‘ĪĽĹ‚ėč≤ĘĪĽ÷ō–¬Ĺ®ėč°£ń„Ņ…“‘į—ňŁ“ēěť“’`◊x”°Ę“∆ę“䔣¨“≤Ņ…“‘į—ňŁ“ēěť“ŐŠ–—”°Ę“ļŰÜĺ”——“ĺęł…”ĽÚ‘S «ő“Ķń“Ľ≤Ņ∑÷£¨Ňc∆šį—ňŁŹōĶ◊ŕs◊Ŗ£¨≤Ľ»Á‘ ‘SňŁīż‘ŕń«ņÔ¬†Źńő“ĶńļŰÜĺ°£ŇcīňÕ¨ēr£¨ő“ŖÄ’’ė”ēĢ»•įl(f®°)’Ļ◊‘ľļ£¨◊Ć…ķ√ŁŌŮ«ß√śč…Õř“Ľė”ōSĚMļÕ∂ŗ≤ °£ő“£¨”ņŖhīů”ŕ“ĺęł…”£Ľń„£¨“≤”ņŖhīů”ŕń«āÄĄe»ňĶń’fřo°£
ƶ܊£¨“ŅŅ◊V”√√ľąļÕ“ĆWŃēļ√”Ļ√ńÔ£¨“‘ľį∆šňŻĶńŇů”—āÉ£Ņ
ĀŪįŽ∑÷
“Źä”£¨¬†∆ūĀŪÕ¶’żń‹ŃŅĶń“ĽāÄ◊÷£¨Ķę «ő“Ösļ‹”ĎÖíňŁ°£
÷‹áķĶń»ňēĢ”√“Źä”ĀŪ–ő»›ő“£¨‘ŕňŻāÉŅīĀŪ£¨ń≥–©∑Ĺ√śő“ī_Ććļ‹“Źä”£ļő“ÖĘľ”Ńňļ‹∂ŗł–Ňd»§ĶńŇŗ”Ė£¨Ć¶”ŕļ‹∂ŗ»ňĀŪ’f£¨Ŗ@ «≤ĽŅ…ňľ◊hĶń ¬£¨“Úěťń„ «◊‘ľļŐÕ—ŁįŁ£¨ļőĪōńō£Ņő“áL‘á÷Ýť_ĪŔ“ĽāĻꖬĶńÓI”Ú£¨ģĒ»Ľ“≤‘‚ĶĹŃňļ‹∂ŗ»ňĶńŔ|(zh®¨)“…£¨įŁņ®ť_’Ļ–¬ŪóńŅĶńērļÚ ‹ĶĹ∑N∑N◊ŤďŌ£Ľő“Ķńļ√∆ś–ńļ‹÷ō£¨ĪĽ»ňŇķ‘u–gėI(y®®)üoĆ£Ļ•……»Áīň∑N∑N£¨ő“Ķńňý◊ųňýěť‘ŕ÷‹áķ»ňŅīĀŪ «āÄģźÓź£¨∂Ýő“”÷ĆŔ”ŕ’Jú ŃňĺÕą‘∂®ąŐ(zh®™)÷ÝĶń»ň£¨ňý“‘ĪĽļ‹∂ŗ»ňĻŕŃň“Źä”Ŗ@āÄ‘~°£
“‘«į£¨ő“Ķńī_łś‘V◊‘ľļ“™Źä£¨ő“ēĢĪMŃŅ’f∑ĢļÕő““‚“ä≤Ľ“Ľė”Ķń»ň£¨ő“ēĢ”√ļ‹ŅžĶń’ZňŔļÕŹäŃ“Ķń’Zö‚įĶ ĺƶ∑Ĺ——ő“ «Ć¶Ķń°£Ķę «Ŗ@é◊Őž£¨ő“”–Ńň≤ĽÕ¨ĶńŅī∑®°£◊ÓĹŁÖĘŇcŃň“ĽāÄŪóńŅ£¨ «‘ŕŔY‘īÖT∑¶Ķń«ťõrŌ¬◊Ų“ĽąŲĻę“śÕ∆ŹVĽÓĄ”£¨Ć¶”ŕő“ļÕő“ĶńĽÔįť∂Ý—‘£¨ÓH”–“į◊ ÷∆ūľ“”Ķń“‚ő∂£ļŖÄõ]’“ĶĹļŌ◊ųÜőőĽ£¨õ]”–ļ√ĶńļŌ◊ų∑Ĺ Ĺ£¨…ŪŖÖ»Ī∑¶ąF͆£¨»Ī∑¶ŔYĹū……÷‹áķĶńŇů”—ľäľä“Úěť“ÍP–ń”∂ÝĄŮő“£¨Ŗ@āÄŪóńŅ≤ĽŅ…ń‹≥…Ļ¶£¨ń„≤Ľ“™≥—ŹäŃň°£∂Ő∂ŐÉ…ŐžĶńērťg£¨É…āÄŇů”—∂ľ‘ŕ’f“≤Ľ––”°Ę“≤ĽŅ…ń‹”£¨≤ĽŖ^ő“ŖÄ «ń‹ČÚ’{(di®§o)’Ż†ÓĎB(t®§i)£¨ņ^ņm(x®ī)ĪŪ¨F(xi®§n)Ķ√ļ‹“Źä”£¨ļÕő“Ķń∆šňŻŇů”—ņ^ņm(x®ī)—–ĺŅ°£Ķę «£¨ő“ņ^ņm(x®ī)‘‚ĶĹīÚďŰ°£÷ĪĶĹĶ໿՞£¨ő“ĺŕÜ ĶĹėOŁc°£
”ŕ «ő“ť_ ľÜĖ◊‘ľļ£¨ő“≤ĽŹäÜŠ£Ņő“≤Ľ «Õ¶”–◊‘–ŇĶńÜŠ£Ņő“≤Ľ «ļ‹‘ł“‚áL‘áļÕŐŰĎū(zh®§n)–¬ ¬őÔÜŠ£ŅĶę «ģĒő“ť_ ľžoŌ¬–ńĀŪ¬ż¬żĶō∑īňľ◊‘ľļ£¨ő“≤Ňįl(f®°)¨F(xi®§n)£¨‘≠ĀŪ£¨ő““™’ś’ż√śĆ¶Ķń «◊‘ľļÉ»(n®®i)–ńĶń“≤ĽŹä”°£ ¬Ćć…Ō£¨õ]”–“ĽāÄ»ňń‹‘ŕňý”–∑Ĺ√ś∂ľń«√ī“Źä”°£∆šĆćő“Ņ…“‘≥–’J◊‘ľļĶńīŗ»ű£¨≥–’J◊‘ľļĶńń‹Ń¶ «”–ŌřĶń°£“Ľ«–‘ŕ”ŕ◊‘ľļ£¨ «∑Ů◊„ČÚŃňĹ‚◊‘ľļĶńŖÖĹÁ£¨◊‘ľļĶńń‹Ń¶°£
ģĒő“◊„ČÚŃňĹ‚◊‘ľļĶńērļÚ£¨ő“ť_ ľ’\ĆćĶō√śĆ¶ńŅ«įĶń«ťõr£¨»Ľļůő“÷™Ķņ£¨ērôC≤Ęõ]”–’ś’ż≥… ž£¨ļ‹∂ŗŔY‘īŖÄļ‹ÖT∑¶°£ ¬Ćć…Ō£¨ő“õ]”–ń«√ī“Źä”£¨’śĶńõ]”–°£ľ»»Ľõ]”–ń«√ī“Źä”£¨ń«ĺÕŐĻ»ĽĶō≥–’Jį…£¨Ŗ@≤Ę≤Ľ”–ďp”ŕő“Ķń–őŌů°Ęő“Ķń√ś◊”£¨÷Ľ «ń‹ČÚŐŠ–—◊‘ľļ£¨ő“Ņ…“‘◊Ų–© ≤√ī◊ĆŖ@ľĢ ¬«ť◊ÉĶ√łŁļ√£¨∂Ý≤Ľ «ŌŮ“Ľ÷ĽľąņŌĽĘ£¨ļ√ŌŮľ‹Ą›Íá’Őņ≠Ķ√ļ‹īů£¨∆šĆć“ĽÕĪĺÕ∆∆°£ňý“‘£¨≥–’J◊‘ľļ“»ű”ĽÚ’Ŗ“≤Ľ––”£¨Ŗ@≤Ň–Ť“™”¬ö‚°£
ő“ļÕŇů”—’{(di®§o)’ŻŃňńŅėňļÕ∆ŕīż£¨¨F(xi®§n)‘ŕĶńő“āÉ£¨Žm»Ľ«ťõrŖÄ «õ]”–Őęīůļ√řD£¨Ös◊ÉĶ√łŁ”––Ň–ń£¨“Úěťő“āÉ◊„ČÚ’\Ćć°£
ňý“‘ő“≤ĽŌ≤ög“Źä”Ŗ@āÄ◊÷£¨ŽyĶņ“Ľ«–ĶńÜĖÓ}∂ľ“™”√“Źä”ĀŪ√śĆ¶ÜŠ£Ņ»ÁĻŻ”√“Źä”ĀŪĹM‘~Ķń‘í£¨ń„ń‹ŌŽĶĹ ≤√ī£Ņ“Źäļ∑”£¨“ŹäĄ›”£¨ŖÄ «“Źä‘~äZņŪ”£Ņ¬†∆ūĀŪ∂ľļ‹“”≤”Ķńł–”X£¨»Ī∑¶Źó–‘£¨»Ī∑¶ž`ĽÓ£¨ļ√ŌŮ“≤»Ī∑¶ōS”ĮŇc≥šĆć°£Ōŗ∑ī£¨’\ĆćĶōĶÕŌ¬Ó^ĀŪ£¨ŅīŅī◊‘ľļĶńń_Ō¬£¨ŅīŅī÷‹áķĶń≠h(hu®Ęn)ĺ≥£¨≤Ňń‹łŁľ””–ѶŃŅ°£
¨F(xi®§n)‘ŕő“÷™ĶņŃň£¨ģĒ√śĆ¶≤ĽŔĚÕ¨Ķń¬ē“Űēr£¨ő“≤Ľ”√“Ľ∂®ĪŪ¨F(xi®§n)Ķ√ŐōĄe“Źä”£¨‘áąD”√’Z—‘ĀŪ’f∑ĢňŻ£¨“Úěť––Ą”ļÕĹYĻŻēĢ «◊Óļ√Ķńīūįł£ĽģĒő“…ÓŌ›≤ĽņŻŐéĺ≥ēr£¨“Źä”“≤≤Ľ «ĪōŪöĶń£¨“≤‘SŌ»“™≥–’Jő“Ķń“»ű”£¨≤Ňń‹łŁļ√Ķōņ^ņm(x®ī)£¨ĪŪ√śĶń“Źäļ∑”≤Ę≤Ľń‹Ĺ‚õQÜĖÓ}°£ő“ĶĻ «”XĶ√£¨“Ūg”Ŗ@āÄ‘~≤ĽŚe£¨“Úěťń„ń‹ŅīĶĹ£¨ĺÕ «ń«“ĽŁcŁcĶńą‘≥÷ļÕ“ĽŁcŁcĶńҨѶ£¨ő“Ķń√ųŐžĺÕēĢ◊ÉĶ√≤Ľ“Ľė”°£
ĪůĪůĻ√ńÔ
ďĢ(j®ī)’fŅš“ĽāÄĻ√ńÔ£¨◊Óļ√ «Ņšňż∆ĮŃŃ£¨»ÁĻŻ≤Ľ∆ĮŃŃ£¨Ņ…“‘Ņšňż”–ö‚Ŕ|(zh®¨)£¨»ÁĻŻŖ@“≤õ]”–£¨Ņ…“‘’fňż…∆Ńľ£¨‘Ŕ≤ĽĚķ£¨ĺÕ’fń„’śĹ°ŅĶ°£ļ‹Ņ…Ōߣ¨Źń–°ĶĹīů£¨Ŗ@–©√ņļ√Ķń–ő»›‘~∂ľŇcő“üoÍP°£īů»ňāÉ“äĶĹő“£¨üo“ĽņżÕ‚∂ľēĢ”√∑«≥£ŅšŹąĶń’Z’{(di®§o)ƶő“į÷čĆ’f£ļ“ń„ľ“–°ļĘĆWŃē’śļ√£°”»Ľļůņ≠Ŗ^◊‘ľ“ļĘ◊”£¨’Z÷ō–ńťLĶōĹŐ”żĶņ£ļ“ń„ŅīŅī»ňľ“”Ŗ@“ĽŅŐ£¨Źńń«–©–°ń–…ķ–°Ňģ…ķ…šĀŪĶńšJņŻńŅĻ‚÷–£¨ő“ĺÕ÷™Ķņ◊‘ľļ‘Ŕīő≥…Ńň≤Ľ ‹ög”≠Ķń“Ąe»ňľ“Ķń–°ļĘ”°£
“ĆWŃēļ√” «“Ľĺšńß÷š£¨Ôh é‘ŕő“Ķń’ŻāÄ«ŗīļ∆ŕ°£ģĒ»Ľ“ĆWŃēļ√”≤Ľ «Čń ¬£¨Ņ…“ĽāÄĻ√ńÔ‘ŕĄe»ň—ŘņÔ»ÁĻŻ÷Ľ”–“ĆWŃēļ√”Ŗ@āÄÉě(y®≠u)Łc£¨āÄ÷–◊Őő∂£¨“Ľ—‘ŽyĪM°£
…Ō–°ĆWēr£¨–‘Ąe“‚◊R…–Őé”ŕń£ļżŽA∂ő£¨ő“ŹńÓ^ĶĹń_ĽýĪĺļÕń–ļĘ◊”üoģź——∂Őįl(f®°)°ĘŖ\Ą”∑Ģ°ĘŖ\Ą”–¨£¨ŹńĀŪ≤Ľī©»Ļ◊”°£Ŗ@∑N«ťõr‘ŕŃýńÍľČēr≥Ų¨F(xi®§n)ŃňőĘ√ÓĶń◊ÉĽĮ£¨”–ĶńŇģļĘť_ ľ–Ŗ–ŖīūīūĶō≤Ľ…Ōůw”ż’n£¨÷Ľś≥ś≥ś√ś√Ķō’ĺ‘ŕ“ĽŇ‘Ņī÷Ýő“āÉŇ‹≤Ĺ°£÷iĶ◊‘ŕ“ĽĻĚ(ji®¶)…ķņŪ–l(w®®i)…ķ’nļůĪĽĹ“ē‘£¨ő“ÕĽ»Ľ“‚◊RĶĹ£¨ő““≤ «āÄĻ√ńÔ°£÷™Ķņ’śŌŗĶńő“≤Ę≤ĽŅžė∑£¨“Úěť‘ŕ–°ĆWģÖėI(y®®)ļůĶńń«āÄ ÓľŔ£¨ő“łķ÷Ýį÷į÷»•…ŐĶÍŔIŽäÔL…»£¨ĶÍľ“üŠ«ťĶō’–ļŰő“į÷£ļ“ń„łķń„Éļ◊”◊Ý÷Ý–™ēĢÉļ£¨ő“»•ā}éžĹoń„ń√–¬Ķń°£”
…Ō≥ű÷–ļů£¨ő““ņ»Ľ «∂Őįl(f®°)£¨÷Ľ «Ňľ†Ėį—Ŗ\Ą”—ĚďQ≥…Ň£◊–—Ě°£ń«ērļÚň∆ļű”–āÄ≤Ľ≥…őńĶń“é(gu®©)¬…£¨‘ĹźŘīÚįÁĶńŇģ…ķĆWŃē‘Ĺ≤Ľļ√£¨»ÁĻŻį—“źŘīÚįÁ”ďQ≥…“∆ĮŃŃ”£¨‘ŕņŌéü—ŘņÔĻņ”č“≤ «“Ľė”Ķń“‚ňľ°£ņŌéüāÉļ‹Ō≤ögő“£¨ŅāŅšő““ĆWŃēļ√”°£»ÁĹŮĽō ◊£¨”–ŁcŅ÷≤ņ°£
“ĽŐž∑ŇĆWļů◊Ų÷Ķ»’£¨ő“ļÕ“ĽāÄŇģÕ¨ĆW‘ŕĹŐĆWė««įĶń“Ľ∆¨Ņ’ĶōíŖĶō°£“ĽČ¶÷ģłŰ «“Ľňý¬öėI(y®®)ĆW–££¨ņÔ√śĶńĆW…ķńÍľoĪ»ő“āÉīů£¨ģĒ»Ľ“≤łŁ“≥… ž”°£é◊āÄń–…ķ唳ŖŇRŌ¬£¨į—Ó^ŐĹ≥ŲīįĎŰ£¨õ_ő“āÉīĶŅŕ…ŕ°£ŇģÕ¨ĆWň∆ļű≤Ľ «Ķŕ“ĽīőĹõ(j®©ng)övÓźň∆ ¬ľĢ£¨ļÕňŻāÉŖÄ”–ēŠ√ŃĽ•Ą”°£Ŗ@“ĽńĽĪĽ40∂ŗöqĶńįŗ÷ų»őŅīĶĹŃň°£‘ŕĶŕ∂ĢŐžĶń‘Á◊‘Ńē…Ō£¨ňżŁc√ŻĶņ–’Ķō’f£ļ“×××£®÷łŇģÕ¨ĆW£©◊Ų÷Ķ»’£¨∂ľ“™ļÕĄe»ňł„≤Ľ«Ś≥Ģ£°”ŇģÕ¨ĆW–°¬ēřqĹ‚£ļ“ «ňŻāÉ?n®®i)«ő?hellip;…”įŗ÷ų»ő“Ľ¬†łŁö‚Ńň£ļ“ŅŌ∂® «ń„◊‘ľļ’–ĀŪĶń£¨≤Ľļ√ļ√◊xēÝ’ŻŐž≤Ľ÷™Ķņ‘ŕł…¬Ô£°ń„ŅīŅī»ňľ“×××£®÷łő“£©£¨‘ű√īõ]”–ń–…ķ»«ňż£°”
¬łŰ∂ŗńÍ£¨ő“‘Á“—ÕŁŃň≥ű÷–ń√Ŗ^∂ŗ…Ŕ™Ą£¨ŅľŖ^∂ŗ…ŔĶŕ“Ľ£¨”õĎõ™q–¬Ķń÷Ľ”–įŗ÷ų»őĶńŖ@ĺš‘í°£ő““Ľ÷ĪŌŽģĒ√śÜĖňż£ļ“ņŌéü£¨ńķī_∂®Ŗ@ «‘ŕŅšő“ÜŠ£Ņ”∆šĆć£¨ģĒērő“ļÕįŗ…Ōé◊āÄĽž…ÁēĢĶńń–…ķÍPŌĶ“≤≤ĽŚe£¨“Úěťő“ŹńĀŪ≤ĽīÚňŻāÉĶń–°ąůłś£¨ŖÄ≥£≥£ĹŤ◊ųėI(y®®)ĪĺĹoňŻāÉ≥≠°£ňŻāÉƶő“ļ‹ŅÕö‚£¨≤ĽĹoő“»°ĺbŐĖ£¨ŖÄ◊ū∑Qő“ěť“ļ√ĆW…ķ”£¨Ņ… «ŹńĀŪ≤Ľéßő““Ľ∆ūÕś°£
ĶĹŃňłŖ÷–£¨ő“ŃŰ∆ūŃňťLįl(f®°)£¨Ňľ†Ėī©āÄ»Ļ◊”°£Ňů”—»¶÷–£¨∂ľ «ļÕő““Ľė”÷–Ńň“ĆWŃēļ√”ńß÷šĶńļĘ◊”£¨ő“āÉ”–“ĽāÄĻ≤Õ¨ńŅėň——ł…ŁcÉļČń ¬°£»Ľ∂Ý£¨ľīĪ„ő“Ļ‚√ų’żīůĶō“‘ÁĎŔ”£¨Źń≤ĽÖĘľ”ÕŪ◊‘Ńē£¨…ű÷ŃŐĖ’Ŕ»ęįŗÕ¨ĆWĹo–£ťLĆĎ–Ň“™«ůŃT√‚≤ĽŌ≤ögĶńįŗ÷ų»ő£¨ņŌéüāÉ∂ľ «Ī†“Ľ÷Ľ—Řť]“Ľ÷Ľ—Ř°£
√ŅīőŽSį÷čĆ≥Ų»•ĺŘ≤Õ£¨Ķę∑≤”–ő“ļÕ∆šňŻŇģļĘÕ¨◊ņ£¨Ć¶∑Ĺ“Ľ∂®ēĢę@Ķ√“∆ĮŃŃ”ĶńŔĚ’Z°£“Úěť“ĆWŃēļ√””ņŖhĆŔ”ŕő“£¨≤ĽĻ‹ő“÷ģ«įĽ®Ńň∂ŗ…ŔērťgõQ∂®ī©ńńľĢ“¬∑Ģ°£Ŗ@ė”Ķń»’◊”£¨ő“Ŗ^Ńň12ńÍ£¨÷ĪĶĹĀŪĪĪĺ©ńÓīůĆW£¨…ŪŖÖ≠h(hu®Ęn)ņ@÷ÝĪä∂ŗáÝľ“ľČĶńĆWį‘£¨“ĆWŃēļ√”≥…Ńň◊ÓīůĶńł°‘∆°£
‘ŕŖ@āÄģĒērń–ŇģĪ»ņż6°√1ĶńīůĆWņÔ£¨‘໎ĆW≤Ľĺ√ļůĶń–¬…ķőŤēĢ…Ō£¨ĺÕ”–ń–…ķÜĖő““™ ÷ôCŐĖ°£÷ģļůĶńöq‘¬÷–£¨Žm»Ľń„≤Ľ∆ĮŃŃ£¨Ņ… «ēĢ”–»ňŅšń„Ņ…źŘ£Ľń–ļĘ◊”≤Ľ‘ŔŌÚń„’ąĹŐŖ@ĶņÓ}‘ű√īĹ‚£¨∂Ý «ēĢÜĖń„Ŗ@ ◊łŤł–”X‘ű√īė”£ĽŖBő“◊‘ľļ∂ľĶŕ“Ľīő÷™Ķņ£¨‘≠ĀŪ≥żŃň“ĆWŃēļ√”÷ģÕ‚£¨ő“ŖÄ”–Ŗ@√ī∂ŗĶńÉě(y®≠u)Łc£ļő“–¶∆ūĀŪ—Řĺ¶ «ŹĚĶń£¨ő“’f‘íļ‹úō»Š£¨ő“∂ģĶ√’ś∂ŗ——√Ż»ň›W ¬°Ęöv ∑įňō‘£¨ő“ģčģčĺÄólļ‹ň¨ņŻ£¨ő“…∆”ŕ ’ įő›◊”……Ŗ@≤Ň «“ĽāÄ’ż≥£ĶńĻ√ńÔĎ™‘ďďŪ”–Ķń∑QŔĚį°£°
ĹY ÝŃňĆW…ķ…ķ—ń£¨“ĆWŃēļ√”Ķńėňļě◊‘»Ľ¬ż¬żŌŻ ߣ¨≤ĽŖ^ďĢ(j®ī)’f‘ŕő“◊xŖ^Ķń≥ű÷–°ĘłŖ÷–£¨»‘»ĽŃųāų÷Ýő“ĶńĻ ¬°£Ōŗ–Ň‘ŕŖ@–©90ļů°Ę00ļůļĘ◊”ĶńŌŽŌů÷–£¨ő“īůłŇ «“ĽāÄ÷ĽēĢńÓēÝ°ĘļŃüo«ť»§£¨ÍPśI «ťLĶ√ŅŌ∂®≤Ľ‘ű√īė”ĶńīŰįŚ—Řĺ¶√√°£ĹŤīňőń£¨Žp—ج„“ē5.1Ķńő“ŌŽ’f£¨≤Ľ“™ĪĽ“ĆWŃēļ√”ĶńŤFńĽ—ŕ…wŃň…ķ√ŁĶń»§ő∂–‘£¨“ĆWŃēļ√”ĶńĻ√ńÔ“≤”–“ĽÓwÚ}Ą”Ķń–ńį°£°
»Ô≤A
”÷ĶĹŃňĹĽŅāĹY°ĘĆĎ‘u’Z°Ę‘uŌ»ŖMĶńērļÚ°£
Ļ§◊ųŃňé◊āÄńÍÓ^ļů£¨įl(f®°)¨F(xi®§n)◊‘ľļĆĎĶńŅāĹYļÕ≤ŅťT÷ų»őĹoĶń‘u’Z∂ľ“—¬š»ŽŮĹĺ ——ő“‘ŕĹŁ3∑›ńÍĹKŅāĹYņÔ∂ľĆĎĶņ£ļ“Ŗ^»•Ķń“ĽńÍ£¨ő“ĽýĪĺ◊ŲĶĹŃňĆ£ėI(y®®)£¨Ĺ”Ō¬»•Ď™‘ď «ĺīėI(y®®)°ĘźŘėI(y®®)°Ęė∑ėI(y®®)……”ĶęĻ§◊ų†ÓĎB(t®§i)ŖÄ «Õ£ŃŰ‘ŕ¬öėI(y®®)ĶńťTôĎ…ŌīÚřD°£≤ŅťT÷ų»őĶń‘u’ZÕ®≥£ēĢłŁĹo√ś◊”“Ľ–©£ļ“Ľĺš“źŘćŹĺīėI(y®®)” «ŅŌ∂®ő“ĶńĻ§◊ų†ÓĎB(t®§i)£¨‘ŔĀŪ“Ľĺš“ė∑”ŕ∑ÓęI” «ĪŪďPő“‘ŕÕÍ≥…Īĺ¬öĻ§◊ų÷ģÕ‚£¨ŖÄė∑“‚ÖĘŇc“Ľ–©∆šňŻ≤ŅťTĶńėI(y®®)Ą’°£
÷ų»őŅ…ń‹≤Ľ÷™Ķņ£¨∆šĆć£¨ő“”ĎÖíĄe»ň’fő““ė∑”ŕ∑ÓęI”£¨”»∆š «“∑ÓęI”Ŗ@āÄ‘~°£Ŗ@ė”Ķń‘uÉrļ‹Ņ…ń‹◊ĆĄe»ň’`“‘ěťő“ļ‹üoňĹļ‹łŖ…–£¨Ķęő“÷Ľ «ļÕļ‹∂ŗńÍ›p»ň“Ľė”£¨≤Ľ÷Ľį≤”ŕ‘ŕĪĺ¬öćŹőĽ…Ō—≠“é(gu®©)Ķłĺō£¨“≤ēĢ‘॒ÕÍ“’żėI(y®®)”÷ģ”ŗ£¨Ň‹»•∆šňŻ≤ŅťT∆šňŻÓI”ÚáLűrůwÚě“Ľį—°£
ģĒ»Ľ£¨»•Ąe»ňĶńĶōĪP…Ō≤šąŲ◊”»ŲögÉļ «”–ÔLŽUĶń°£‘ŕõ]”–ÕÍ≥…Īĺ¬öĻ§◊ų÷ģ«į£¨ő“ «Ēŗ»Ľ≤ĽēĢ»•–÷Ķ‹≤ŅťTĒąĽÓÉļĶń£¨√‚Ķ√ĹoŪĒÓ^…ŌňĺŃŰŌ¬ŅŕĆć°£
Ŗ@“≤ «Ĺõ(j®©ng)övŖ^ĹŐ”ĖĶń°£ĄāŖMÜőőĽēr£¨“Ľ «≥Ų”ŕ◊‘ľļĶńļ√∆ś–ń£¨∂Ģ «”–Ķń≤ŅťT“≤ī_Ćć»Ī»ň ÷£¨”ŕ «ĺÕēĢ”––÷Ķ‹≤ŅťTĶńōďōü»ňňĹŌ¬’“ő“?gu®©)Õ√¶°£ńÍ›p»ň¬Ô£¨ĺęѶ≥š◊„«“ļ√’f‘í£¨“ĽŅŕĎ™≥–Ō¬ĀŪ°£ĹYĻŻńō£¨◊‘ľļõ]∑÷«Ś»őĄ’Ķń›p÷ō叾Ī£¨įīērĹĽŃňĄe»ňĶńĽÓÉļ£¨ÖsĶĘ’`Ńň◊‘ľ“Ķń’żĹõ(j®©ng) ¬£¨◊Ć÷ĪŌĶÓIĆßĒĶ(sh®ī)¬šŃňįŽŐž≤ĽĄ’’żėI(y®®)°£
Ŗ@∑N“łŻŃňĄe»ňĶńĶō£¨ĽńŃň◊‘ľ“ĶńŐÔ” ĹĶńŚe’`£¨∑łŖ^“ĽīőÉ…īő“≤ĺÕťL”õ–‘Ńň°£∂Ý«“–÷Ķ‹≤ŅťTÕýÕý“≤ēĢÓI«ť£¨Ĺoő“”õ…ŌÓ~Õ‚ĶńĻ§∑÷£¨ň„≤ĽĶ√∑ÓęI°£ĶęŖÄ”–“Ľ∑N“≤Ľ’ą◊‘ĀŪ”Ķń∑ÓęIĺÕõ]ń«√ī»›“◊ťL”õ–‘£¨ńńҬƶ∑Ĺ?j®©ng)]”–»őļőĪŪ ĺ£¨◊‘ľļ∂ľēĢŌŽ∑Ĺ‘O∑®»•ľ”»Ž£¨”√¨F(xi®§n)‘ŕĶńŃų––’Z’fĺÕ «£ļŖ@Ĺ–’śźŘ°£
ő“ «ĺęѶ¬‘”–Ŗ^ £Ķń»ň£¨“ĽĶ©–ńņÔ”–Ī»›^–¬űrĶńŁc◊”£¨«“ĆŔ”ŕń‹Ī„ņŻňŻ»ň‘žł£ľĮůwĶńń«∑N£¨ĺÕļ‹”–ĆĘňŁĆć¨F(xi®§n)Ķńõ_Ą”°£łŁ““™√Ł”Ķń «£¨ő“≤Ę≤ĽĚM◊„“ĽāÄ»ňhigh£¨ŅāēĢ◊ß…Ōé◊āÄļ√”—“Ľ∆ūÕśÉļ∆Ī°£“Ú∂Ý£¨»ÁĻŻő“”XĶ√ÜőőĽņÔĶńń≥–©ŔY‘ī…–”–ĚďѶť_įl(f®°)£¨ĽÚ «◊‘ľļŌ»«įĶńĹõ(j®©ng)Úě∑eņŘń‹ěť∆šňŻ≤ŅťTňý”√£¨ĺÕ‘ŕėI(y®®)”ŗērťg÷ųĄ”ęI”čęI≤Ŗ°£”–ÓIĆßƶīň“≤ĹoŖ^ĻńĄÓ£ļ“ńÍ›p»ňĶń–ń“™“į“Ľ–©£¨≤Ľ“™į—ńŅĻ‚÷Ľ∂Ę÷Ý◊‘ľļĶńėI(y®®)Ą’ÓI”Ú£¨“™ł“”ŕ∂ŗŌŽ∂ŗ◊Ų°£”
ĪMĻ‹Ŗ@∑N≤Ľ”軎ŅÉ–ßŅľļň£¨…ű÷Ń“≤üo∑®ĆĎŖMńÍĹKŅāĹYĶń––ěťŔMērŔMѶ£¨“≤ļ‹ŽyĶ√ĶĹÜőőĽĻŔ∑ĹĶń’JŅ…£¨Ķęő““ņ»Ľė∑īň≤Ľ∆£°£ēr≤ĽērĪĽő“◊ß…Ō“Ľ∆ū’ŘÚvĶń“ĽőĽ–°ĽÔįťĆ¶īň”–Ŗ^ĺęĪŔĶń∆ őŲ£ļĺÕ3āÄ◊÷£¨“ő“ė∑“‚”°£ňż’fĶ√ƶ£¨ő“āÉ∑÷ŌŪ≥…ĻŻŖÄ’ś≤Ľ «ěťŃň ≤√īĪŪďPļÕ™ĄĄÓ——«ßĹūŽyŔI“ő“ė∑“‚”£¨◊‘ľļť_–ń◊Ó“™ĺo°£
ňý“‘£¨ő““™į›Õ–ĆĎ‘u’ZĶńłųőĽÓIĆߣ¨Ņ…Ąe‘ŔŅšŔĚő“āÉ‘ŕĻ§◊ų…Ō“ė∑”ŕ∑ÓęI”Ńň°£“∑ÓęI” «“Ľ∑N≤ĽŅ…‘Ŕ…ķŔY‘ī£¨≤Ľń‹÷łÕŻ√Ņ»ň∂ľēĢė∑“‚£¨√ŅĽō∂ľ”–ů@Ō≤°£∂Ýő“āÉňýė∑“‚◊ŲĶń£¨÷Ľ≤ĽŖ^ «ěťŃň”š»ňźāľļ£¨Ĺ‘īůögŌ≤°£
Õű–°–°
ő“’śĶńü©ÕłŃň“ŅŅ◊V”Ŗ@āÄ‘~°£¬†…Ō»•ŌŮ «įż™Ą£¨ĆćŽH…ŌÖs «“Ľ∑N«ŰĹŻ°£
≤√īň„“ŅŅ◊V”£ŅĪ»»Á£¨Ī£◊C’J’śÕÍ≥…ņŌéüŃŰĶń◊ųėI(y®®)£¨ŅŌ∂®ĚM◊„ľ“ťL∆ŕÕŻŅľ…Ō÷ōŁcīůĆW£¨Ĺ^≤Ľĺ‹Ĺ^ÓIĆßŇ…Ō¬ĀŪĶń»őĄ’……Ņā÷ģ£¨ĺÕ «¬†’–ļŰ°Ęōďōü»ő°Ę ō“é(gu®©)ĺō£¨ĺÕ «“ń„řk ¬£¨ő“∑Ň–ń”£¨ĺÕ «“įŁĺżĚM“‚”°£
Źń–°ĆWť_ ľ£¨ő“ĺÕŪĒ÷ÝŖ@É…āÄ≥Ń÷ōĶń◊÷°£◊ųěťįŗł…≤Ņ£¨◊‘Ńē’n…Ōő“ŤF√śüoňĹĶōéÕņŌéüĺS≥÷÷»–Ú£¨įŗēĢĽÓĄ”ērĺ§ĺ§ėI(y®®)ėI(y®®)ĶōéÕņŌéüŇŇ—›ĻĚ(ji®¶)ńŅ°£◊ųěťļ√ĆW…ķ£¨ņŌéüÜĖ’lÓAŃē’nőńŃň£¨ő““Ľ∂®ēĢŇűąŲĶōŇe ÷£ĽÓIĆßĀŪ¬†’nēr£¨ő“ĶńĽōīū◊Ó◊ĆņŌéü∑Ň–ń°£
ļŃüo“…ÜĖ£¨ő“ «ņŌéü—ŘņÔĶńŅŅ◊VĆW…ķ£¨Ķę‘ŕÕ¨ĆW–ń÷–£¨ő“≤Ę≤Ľ ‹ög”≠°£“Úěť“◊V”ĺÕ «“ĽłŮ“ĽłŮ°ĘüoŐé≤Ľ‘ŕĶń“é(gu®©)ĺō°£
ń≥ńÍĹŐéüĻĚ(ji®¶)«įŌ¶£¨ő“āÉįŗÕ¨ĆW∑ŇĆWļů’ĺ‘ŕ–£ťTÕ‚…ŐŃŅ‘ďĹoįŗ÷ų»őňÕ ≤√ī∂YőÔ°£ń«ēr£¨ĆW–£łĹĹŁŖÄõ]”–ŅŌĶ¬Ľý°ĘĪōĄŔŅÕļÕĪ‹ÔLŐŃ£¨ÉH”–Ķń–›ťeä ė∑ąŲňýĺÕ «é◊āÄŔuł…īŗ√śļÕüoĽ®ĻŻĶń–°Ŕu≤Ņ°£…ķĽÓőĮÜTůwŔNĶō’f£ļ““™≤Ľ‘ŘāÉĽōĹŐ “ņÔ¬ż¬ż…ŐŃŅį…£¨ő“Ŗ@Éļ”–ŤÄ≥◊°£”
“Ľ»ļ»ň‘ÁĺÕ’ĺņŘŃň£¨Ňdõ_õ_ĶōĺÕ“™ÕýĆW–£ņÔ◊Ŗ°£÷Ľ”–ő“’ĺ÷Ýõ]Ą”£¨÷Ķ÷‹…ķĺÕ ō‘ŕ–£ťTŅŕ£¨ő“ĪōŪöĪ£≥÷«Ś–—°£“≤Ľ––≤Ľ––£¨∑ŇĆWļů‘ŔŖMĹŐ “ «ēĢĪĽŅŘ∑÷Ķń£¨‘ŘāÉĺÕ‘ŕŖ@Éļ’fį…°£”ő“ľįēr◊Ť÷ĻŃň«įŖM÷–Ķń͆őť£¨ěťīňŖÄļÕ…ķĽÓőĮÜTīů≥≥Ńň“Ľľ‹°£
“Úěťő“Ķń“ŅŅ◊V”£¨ń«“Ľ÷‹£¨ŃųĄ”ľt∆ž“ņ»ĽŃŰ‘ŕįŗņÔ°£ĶęļůĀŪĶńįŗł…≤ŅłāŖx÷–£¨ő“õ]ń‹ŃŰ◊°īů∂ŗĒĶ(sh®ī)Õ¨ĆWĶńŖx∆Ī°£
…ż»Ž÷–ĆWļů£¨ő“≤ĽŌŽ‘Ŕ“Úěť“ŅŅ◊V”∂ÝĪĽÕ¨ĆWĻ¬ŃĘ°£‘ŕįŗņÔő“õ]”–ďķ»ő»őļő¬öĄ’£¨Ō£ÕŻļÕÕ¨ĆWīÚ≥…“Ľ∆¨°£”ŕ «£¨Õ¨ĆWīÚľ‹ērő“≤Ľ’ĺ͆£¨ņŌéü’{(di®§o)≤ť›õ«ťērő“ń®Ō°ńŗ°£
»f»fõ]ŌŽĶĹ£¨Õ¨ĆWƶő“Ķń‘uÉrŖÄ «“ŅŅ◊V”£¨Ŗ@āÄő“ėOѶŌŽĒ[√ďĶń‘~°£∆šĆć£¨ő“÷Ľ «‘ŕ‘Á…Ō–°ĹM◊Ų÷Ķ»’ērú ēr≥Ų¨F(xi®§n)∂Ý“—£¨“Úěťďķ–ńĪĽĄe»ňōüĻ÷°£–°ĹMąF͆ĆĎ◊ųėI(y®®)£¨Õ¨ĆWāÉ∂ľŌ≤ögłķő““ĽĹM£¨“Úěťő“‘ŕļű≥…ŅÉ°£ňý“‘ģĒ≤ĽŅŅ◊VĶńÕ¨ĆWŇRērŃŐŐŰ◊”≥Ų»•ŐŖ«Ú°ĘĻšĹ÷°ĘŃńīůŐžÉļĶńērļÚ£¨ő“ēĢń¨ń¨Ķōį—◊ųėI(y®®)ņ^ņm(x®ī)Ō¬»•°£ĶĹŃň–°ĹM≥…ĻŻ’Ļ ĺēr£¨‘∆”őĶńÕ¨ĆW≥Ų¨F(xi®§n)Ńň£¨ŖÄőī≤∑Ō»÷™Ķōłķő“’f£ļ“ĺÕ÷™Ķņń„◊ÓŅŅ◊VŃň£°”
‘ĹŅŅ◊VĶń»ňĽÓĶ√‘ĹņŘ°£“Úěť“◊V”ĺÕ «“ĽŹą”…Ąe»ňĶń‘uÉrŅó≥…ĶńĺW(w®£ng)°£ő“Őę‘ŕļűĄe»ňĶńńŅĻ‚Ńň£¨Ņā «Ō£ÕŻĄe»ňĚM“‚£¨≤Ľ∂ģĺ‹Ĺ^£¨◊ÓļůĪĽĺoĺoįŁĻŁ‘ŕŖ@ŹąĺřīůĶńĺW(w®£ng)÷–°£
√ŅāÄ»ň∂ľŌ≤ögń„£¨≤ĽīķĪŪ√ŅāÄ»ň∂ľēĢ”õĶ√ń„°£ģÖėI(y®®)ļ‹∂ŗńÍļůĶń“ĽīőłŖ÷–Õ¨ĆWĺŘēĢ£¨Ó^įl(f®°)“—Ĺõ(j®©ng)į◊ŃňĶńņŌéüŅī÷ÝŖ^»•ĶńĆW…ķ£¨–ņŌ≤Ķō÷ūāÄŁc‘u£ļ“ń„ģĒńÍ∂ľŅžį—ĹŐ “≤ūŃň£¨◊Ćń„ŃP’ĺń„≤Ľļřő“į…°£į•—Ĺ£¨ń„ģĒńÍĺÕĆĎ≤Ľļ√ń«āÄň„–g Ĺ£¨Ĺoő“ľĪĶ√į°°£ń„¨F(xi®§n)‘ŕ’ś «īůĻ√ńÔŃňį°£¨Ī»“‘«į∑Ä(w®ßn)÷ō∂ŗŃň°£”
ĹK”ŕ›ÜĶĹő“Ńň°£ņŌéüÖsÕ£ÓDŃň“ĽŌ¬£¨Ķ≠Ķ≠Ķō’fŃň“Ľĺš£ļ“ń„—Ĺ£¨õ] ≤√ī◊ÉĽĮį°°£”ő“ÕĽ»Ľįl(f®°)¨F(xi®§n)£¨ĹoņŌéüŃŰŌ¬…ÓŅŐ”°ŌůĶń£¨Ņā «ń«–©“≤ĽŅŅ◊V”ĶńĆW…ķ°£ňż…ű÷ŃŅ…ń‹∂ľ≤ĽŐę”õĶ√£¨ģĒńÍ“ĽāÄ’J’ś¬†÷v°ĘįīērÕÍ≥…◊ųėI(y®®)Ķń“ŅŅ◊V”ĆW…ķ « ≤√īė”£¨“ÚěťŖ@ė”Ķń»ňĆć‘ŕŐę∂ŗŃň°£
ő“”––©źěźě≤Ľė∑°£Ôą◊ņ…Ō£¨Ņī÷ÝÕ¨ĆWāÉ ÷őŤ◊„Ķł°ĘŖůŖů‘Ż‘ŻĽōĎõ£¨ģĒńÍ’lļÕ’lěťŃňďĆłŰĪŕįŗĶńŇģ…ķ‘ŕėÚĶ◊Ō¬īÚľ‹≤ÓŁcÉļĪĽĄŮÕň£Ľ’lń√÷ÝíŖį—ģĒľ™ňŻ’ĺ‘ŕ’n◊ņ…ŌĪŪ—›beyondĶńďuĚLė∑£Ľ’l¬N’n»•Õ‚Ķō¬√––£Ľ’lŪĒ◊≤ņŌéüĪĽŇķ‘uěť“ľ‚ŅŐ”……
ő“◊Ý‘ŕ“ĽŇ‘ÕÍ»ę≤Ś≤Ľ…Ō◊ž£¨“ÚěťŖ@–©≥ŲłŮĶń ¬ő““Ľė”∂ľõ]ł…Ŗ^°£ő““Ľ÷ĪŌ£ÕŻ◊ĆĄe»ňĚM“‚°ĘĶ√ĶĹļ√‘u£¨‘ŕŖ@∑NľŔŌůņÔ£¨ő“◊ÉĶ√”Ļ”Ļ≥£≥££¨õ]ŃňāÄ–‘°£ĹK”ŕ£¨◊Ý‘ŕŇ‘ŖÖĶń“ĽāÄŇģ…ķ◊Ę“‚ĶĹő“£¨ňżŇ§Ŗ^Ó^’f£ļ”õĶ√ń«ērņŌéüįl(f®°)Ō¬ĶńĺöŃēĺŪ◊”£¨ń„’nťg10∑÷ÁäĺÕ◊ŲÕÍŃň°£
“ŅŅ◊V”Ŗ@āÄ‘~’śĶń◊Ćő“ ‹ČÚŃň°£¨F(xi®§n)‘ŕő“≤Ň“‚◊RĶĹ£¨‘ŕ∂ŐēļĶń«ŗīļņÔ£¨ń«–©“é(gu®©)ĺōļÕ‘uÉrĺéŅóĶńĺW(w®£ng)£¨◊ÓļůŃŰŌ¬Ķń≤ĽŖ^ «“ĽāÄāÄ∑¶…∆Ņ…ÍźĶńļŕ∂ī∂Ý“—°£
Źąĺßĺß
ő“…ķťL‘ŕ“ĽāÄ‹ä»ňľ“Õ•£¨łł”H «Ņ’‹äÔw––ÜT£¨ńł”H «‹äŠt(y®©)°£◊‘–°‘ŕ≤Ņ͆īů‘ļÉļťLīůĶńļĘ◊”£¨Ņ…ń‹∂ľēĢĹõ(j®©ng)öv“Ľ∑NŌŗň∆Ķń…ķĽÓ∑Ĺ Ĺ——łķŽSłłńłŹń“Ľ◊ý≥« –įŠĶĹŃŪ“Ľ◊ý≥« –£¨‘ŕ≤ĽĒŗįŠľ“ļÕřDĆW÷–∂»Ŗ^ÕĮńÍ°£Ĺõ(j®©ng)≥£įŠľ“Ķń÷ĪĹ”ļůĻŻ «£¨ő“õ]”–Ōŗįť≥…ťLĶń–°ĽÔįť£¨“≤ŹōĶ◊ ß»•ŃňďŪ”–“Ľ∂ő“«ŗ√∑÷ŮŮR”ĶńôCēĢ°£
ő“≥Ų…ķ‘ŕńł”HĻ§◊ųĶńń«āÄŠt(y®©)‘ļ°£ļÕńł”HÕ¨≤°∑ŅĶńŃŪ“ĽāÄ‘–čD∂ŇįĘ“Ő «ő“āÉľ“ŗŹĺ”£¨ňżĶń’…∑ÚļÕő“Ķńłł”H «Ôw––īů͆ĶńĎū(zh®§n)”—£¨ÍPŌĶļ‹≤ĽŚe°£‘ŕŠt(y®©)‘ļīżģa(ch®£n)ēr£¨É…ľ“»ňť_Õś–¶’f£¨»ÁĻŻ «“ĽāÄń–ļĘ“ĽāÄŇģļĘ£¨ĆĘĀŪĺÕ◊Ų”Hľ“°£ ¬«ťĻŻ»Ľ»ÁňŻāÉňý‘ł£¨∂ŇįĘ“Ő…ķŃňāÄīůŇ÷–°◊”£¨∂Ýő“ńł”HÓAģa(ch®£n)∆ŕ“—Ĺõ(j®©ng)Ŗ^Ńňļ√é◊ŐžÖsŖÄŖtŖtõ]”–Ą”žo£¨ňż“Ľ÷ÝľĪ£¨ĺÕįī’’∆ę∑Ĺļ»Ńň–© ≤√ī£¨ő“ĺÕŖ…Ŗ…ČčĶōŃň°£
ģĒ»Ľ£¨Ŗ@–©∂ľ «ļůĀŪ¬†ő“ńł”H’fĶń°£ňżŖÄłś‘Vő“£¨“Úěť◊°Ķ√ĹŁ£¨‘Ŕľ”…ŌÉ…ľ“īů»ň”–“‚üo“‚ĶōīťļŌ£¨ő“ļÕ∂ŇįĘ“Őľ“ĶńĖ|Ė|ŌŮ”H–÷√√“Ľė”–ő”į≤ĽŽxĶōťLīů°£ő“–°ērļÚőłŅŕėOļ√£¨ «āÄŹńőŚŃýāÄ‘¬∆ūĺÕ√ŅŐžļ»»żĹÔŇ£ńŐĶń–°Ň÷—ĺÓ^£¨É…»żöqērĺÕĹõ(j®©ng)≥£◊‘ľļŇ‹»•Ė|Ė|ľ“«√ťT≤šÔą°£Ė|Ė|ļ‹’’Óôő“£¨ľ“ņÔĶńŃ„ ≥∂ľģĒĆöōź“Ľė”≤ō∆ūĀŪ£¨◊‘ľļ≤Ľ…ŠĶ√≥‘£¨Ņā’f“™ŃŰĹo√√√√°£
4öqń«ńÍ£¨łł”Hňý‘ŕĶńÔw––īů͆“™řDąŲĶĹŹąľ“Ņŕ£¨Ė|Ė|“Ľľ“ĄtįŠ»•ŃňńŌ∑Ĺ°£ŽxĄeń«Őž£¨∂ŇįĘ“ŐĪ»ő“ļÕĖ|Ė|ŅřĶ√ŖÄ“™āŻ–ń£¨úI—Ř∆Ňś∂Ķō∂£áŕő“ńł”H“Ľ∂®“™Ī£≥÷¬ď(li®Ęn)ŌĶ°£ő“ĪĽ∂ŇįĘ“ŐĺoĺoĪß÷ÝřD≤ĽŃň…Ū£¨÷Ľļ√–Ī÷Ý—Ř嶔√ńŅĻ‚Ƨ’“Ė|Ė|°£ňŻ™ö◊‘’ĺ‘ŕ“Ľ∂—īÚįŁļ√Ķń––ņÓ÷–ťg£¨ńė…ŌĚM «ĎnāŻ°£ń« «ő“”–…ķ“‘ĀŪĶŕ“Ľīő”XĶ√–ń∂ľ“™ňťŃň°£
ń«āÄńÍīķõ]”–Ľ•¬ď(li®Ęn)ĺW(w®£ng)£¨“≤õ]”– ÷ôC£¨¬ď(li®Ęn)Ĺj∆ūĀŪŅ…õ]”–¨F(xi®§n)‘ŕŖ@√ī∑ĹĪ„°£É…ľ“īů»ňēÝ–ŇÕýĀŪ£¨–ŇņԳۻż≤ÓőŚĺÕēĢäAéß÷Ýő“ļÕĖ|Ė|ĶńĹŁ’’°£É…āÄļĘ◊”ĺÕŖ@ė”łŰ÷Ý»fňģ«ß…Ĺ£¨‘ŕ’’∆¨ņÔłų◊‘≥…ťL°£
ģĒ∂ŇįĘ“ŐŖÄ‘ŕ„Ņ„Ĺ÷Ýń«āÄ√ņļ√ľs∂®ĶńērļÚ£¨5öqĶńő““—Ĺõ(j®©ng)““∆«ťĄeĎŔ”Ńň°£ő“ļ‹ŅžŖmĎ™Ńň‘଱ľ“ŅŕĶń–¬…ķĽÓ°£≤Ņ͆īů‘ļņÔńÍżgŌŗ∑¬ĶńļĘ◊”Īä∂ŗ£¨ő“”»∆šŌ≤ögĪ»ő“–°1öqĶńń–ļĘ‘™Ćö£¨ňŻ «ő“Ķń–°łķįŗ£¨ ≤√ī∂ľ¬†ő“Ķń°£ő“–ń÷–įĶŌŽ£¨»ÁĻŻťLīůļůļÕ‘™ĆöĹYĽť£¨ő“ŌŽ“™ ≤√īĺÕ÷łď]ňŻ»•◊Ųļ√Ńň£¨’ś «ľĢ–“ł£Ķń ¬°£
é◊öqĶńļĘ◊”≤Ę≤Ľ∂ģĶ√źŘ«ť£¨÷Ľ «≥Ų”ŕĪĺń‹£¨Ņ ÕŻ“Ľ∑N”–»ňŌŗįťĶńł–”X£¨Ć¶ő“āÉŖ@–©õ]”––÷Ķ‹Ĺ„√√ĶńļĘ◊”ĀŪ’fłŁ «Ŗ@ė”°£ģĒő“ť_ ľ’J’śŅľĎ]ļÕ‘™Ćö“«ŗ√∑÷ŮŮR”ĶńērļÚ£¨ő“”÷“™įŠĽōĪĪĺ©Ńň£¨∂Ý‘™Ćö“≤≥…Ńň“Ľ∂őŽSÔL∂Ý ŇĶńú\ú\”õĎõ°£
ĺ©Ĺľ—”Ďc‘ŕő“–°ĶńērļÚ «“Ľ∆¨’ś’żĶń ņÕ‚Ő“‘ī£¨–«∂∑ĚMŐž°Ę‘∆Ķ≠ÔL›p°£ő“‘ŕīů…ĹņÔ’™ňŠóó°Ę’ŘŐ“Ľ®°Ę◊ĹŌXŌX£¨ÕśĶ√≤Ľ“ŗė∑ļű°£√ŅāÄ ĘŌń£¨…ĹĶ§Ķ§Ľ®į—īů…Ĺ»ĺ≥…Ńň“ĽÕŻüoŽHĶńľt£¨–žē‘ŰĒĺÕēĢŇű÷Ý“Ľīůį—ĽūľtĶńĽ®ňÕĹoő“°£–žē‘ŰĒĺÕ◊°‘ŕő“ľ“ė«…Ō£¨ňŻčĆčĆ «ő“ĺÕ◊xĶńń«ňý≤Ņ͆–°ĆWĶńįŗ÷ų»ő£¨ňŻį÷į÷Ąt’’ņż «ő“łł”HĶńĎū(zh®§n)”—£¨“ĽāÄłŖīůéõö‚ĶńÔw––ÜT°£ő“įŠĶĹ–¬ľ“ĶńĶŕ“ĽŐžĺÕ’J◊RŃň–žē‘ŰĒ£¨ń«Őžłłńł√¶÷Ý ’ įĖ|őų£¨◊Ćő“◊‘ľļ»•‘ļ◊”ņÔÕś£¨Ľōľ“ĶńērļÚő“◊ŖŚeŃňė«Ć”£¨÷ĪĹ”ŖMŃň–žē‘ŰĒľ“°£
ń«–©»’◊”£¨ő“ļÕ–žē‘ŰĒ“Ľ∆ūŐ”ĆW£¨ ÷ņ≠ ÷◊ŖĪťŃň—”ĎcĶń…ĹĚĺŌ™ŇŌ°£ő“Ņā «ĚMĎ—–“ł£ĶōŌŽ£ļŗŇ£¨ļÕ–žē‘ŰĒ“Ľ∆ū…ķĽÓ“≤≤ĽŚe°£
Ķę «ļůĀŪ£¨ő“”÷įŠľ“Ńň°£
÷ĪĶŨF(xi®§n)‘ŕ£¨√ŅģĒő“ŌŽ∆ūŖ@–©Õý ¬£¨ŅāēĢ”–∑NāŻł–°£≤ĽĒŗÜ ßĶńÕĮńÍļÕ“«ŗ√∑÷ŮŮR”Ŗ@āÄ‘~“Ľ∆ū£¨≥…Ńňő“–ń÷–Ž[Ž[ĶńÕī°£
ĺW(w®£ng)”—”Ď’ď
PR£ļő“◊Ó”ĎÖíĶń‘~ «“ĆWį‘”°£ő“ «“Ľ√Żīů»żĆW…ķ£¨ĀŪ◊‘ōöņßĶńřr(n®ģng)īŚ£¨Źń–°ĺÕ÷Ľ÷™ĶņĆWŃē°ĘŅīēÝ°£»ÁĹŮ…ŌŃňīůĆW£¨Žm…ŪŖÖĶńÕ¨ĆW∂ľ≤Ľ‘ŔüŠ÷‘”ŕ◊xēÝ£¨Ķęő“»‘»Ľ√ŅŐžą‘≥÷ĆWŃē£¨…Ō◊‘Ńē°£“Úěťő“÷™Ķņ◊‘ľļĶń÷™◊Rļ‹ÖT∑¶£¨õ]”–ŔYłŮņňŔMērťg°£ģĒ»Ľ£¨ő““≤ēĢņŻ”√÷‹ń©»•◊Ųľś¬ö£¨ĺöŃē√ęĻP◊÷°£‘ŕÕ¨ĆW—ŘņÔ£¨ő“ «ĆWį‘£¨÷Ľ÷™ĶņĆWŃēĶńĆWį‘°£ő“ł–”XŖ@ «“Ľ∑NĪ…“ń£¨√ŅģĒ¬†ĶĹŖ@āÄ‘~£¨ő“ĺÕ”XĶ√ļ‹≤Ľ ś∑Ģ°£
KiKi-£ļő“◊Ó”ĎÖíĄe»ň’fő““Ņ…Ďz”°£“Úěťľ“Õ•ĶńĺČĻ £¨Źń–°ļ‹∂ŗ»ňŅīĶĹő“£¨—Ř÷–∂ľ≥šĚMŃňĎzĎĎ£¨”–ĶńŖÄ‘ŕő“Ī≥ļůł`ł`ňĹ’Z£¨…ű÷Ńő“Ķńľ“»ň∂ľ“Ľ÷Ī’Jěťő“Ņ…Ďz°£Ķę «ő“≤Ę≤Ľ”XĶ√◊‘ľļŅ…Ďz£¨ő“Ķń…ķĽÓ÷Ľ”–ő“◊‘ľļ”–ôŗņŻ‘uÉr£¨Ąe»ň”÷»Áļőń‹÷™ē‘ő“Ķń–ńńō£Ņ
hi,“¶īů—ņ£ļ‘ŕő“…ŌłŖ»żĶńērļÚ£¨ő“◊Ó”ĎÖíĶń‘~ «“ńXöą”°£≤Ľ÷™Ķņ ≤√ī‘≠“Ú£¨ő“◊ýőĽ”“ŖÖĶńń–…ķť_ ľ∑Qő“ěť“ńXöą”£¨»ĽļůŃŪ“ĽāÄń–…ķ“≤Ŗ@√īļį°£ő“ĺĮłśňŻāÉ≤Ľ“™ń«ė”’fő“°£Ķę «£¨∑«Ķęõ]”–Õ£÷Ļ£¨é◊ļű»ęįŗń–…ķ∂ľť_ ľŖ@ė”∑QļŰő“Ńň°£≤Ľ÷™Ķņ «’śĶń ‹≤ĽŃň£¨ŖÄ «“ÚěťłŖ»żĶńĆWŃēČļѶ£¨‘ŕ“ĽīőÕŪ◊‘Ńē…Ōő“ĹK”ŕĪ¨įl(f®°)Ńň£¨į—◊ņ◊”įŠĶĹŃň◊Óļů“ĽŇŇ°£įŗ÷ų»ő÷™Ķņļů£¨į—ń«É…āÄń–…ķļ›ŇķŃň“ĽÓD£¨∂Ýő““≤‘ŕřkĻę “ņÔŅřŃňįŽāÄ–°ēr°£ļůĀŪ£¨ő“ļ‹…Ŕ‘Ŕ¬†ĶĹ”–»ňļįő““ńXöą”Ńň£¨“Úěťń«īőÕīŅř£¨ő“∑ŇŌ¬Ńň–ń÷–ń™√ŻĶńČļѶ£¨łŖŅľ“≤◊ÉĶ√ŪėņŻŃň°£¨F(xi®§n)‘ŕő““—Ĺõ(j®©ng)īů»żŃň£¨ĽōŌŽ∆ūŖ@ľĢ ¬£¨‘Á“—≤Ľ”XĶ√Ąeҧ°£«įé◊Őž£¨ģĒńÍéßÓ^ļįő““ńXöą”Ķńń«āÄń–…ķ”÷Ŗ@ė”Ĺ–Ńňő“£¨ő“–ń÷–Ös“ĽŌ¬◊”ŠĆ»ĽŃň°£ĆĘĹŁ3ńÍõ]“ä√śŃň£¨ņŌÕ¨ĆW£¨ń„āɨF(xi®§n)‘ŕŅ…ŖÄļ√£ŅģĒńÍĶń“ńXöą”ļ‹ŌŽń„āÉ°£
»‚Ĺz£ļő“◊Ó”ĎÖíĶń‘~ «“Ļ‘«…”°£Ļ«◊”ņÔ£¨ő“≤Ę≤Ľ‘ł“‚◊Ų“ĽāÄ÷–“é(gu®©)÷–ĺōĶńļ√ĆW…ķ£¨ő“Ō£ÕŻ◊‘ľļ’∆ő’»ň…ķ£¨◊Ų◊‘ľļŌ≤ögĶń ¬°£